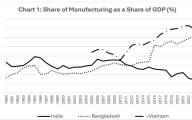金融时报的贾南·加内什在专栏中写道,经济增长显然不能解释一切,否则美国的政治应该比欧洲健康得多,但事实并非如此。

除了那些最顽固的书呆子(他们坚持在2001年1月1日而不是2000年庆祝千禧年)以外,我们现在已经接近本世纪的四分之一了。
到目前为止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25年前人们会觉得难以置信的是什么?
例如,俄罗斯曾经难以支付养老金,如今却成了一台复仇主义的战争机器。
还有另一个例子。美国在经济增长方面超越了欧洲,却并未因此变得更幸福。如果说人们最终是根据物质体验来投票——这似乎是常识——那么美国的政治理应比欧洲,包括英国,更加稳定。
但事实却是,美国与欧洲的反建制民粹主义程度相当,甚至可能更高。
这很奇怪。或许选民是将自己的经济体验与自己的前辈相比,而不是与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人相比。因此,重要的数据是纵向的,而不是横向的。
不过,这种解释并没有让“经济决定政治”的观点显得更加可靠。
想想爱尔兰或波兰。这两个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非主流政党的影响力都在增长。而两国经济却在此期间变得极为富足,几乎无法与(贫穷的)过去相提并论。
上世纪80年代,爱尔兰的新芬党在大选中仅获得1%-2%的选票。到了2000年代,这一比例上升到了约6%。尽管没能取得决定性突破,但这个党在上个月的大选中得票率达到了19%。
与此同时,爱尔兰经济蓬勃发展,从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了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从一个大量移民流出的地方,变成了人们争相前往的地方。
经济决定论者要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这里的唯物主义解释是什么?
可以预见的一种解释是:普遍的富裕可能掩盖,甚至制造了一些具体的困境。
例如,对年轻人来说,更高的住房成本。但这显然是在统计数据中挑选有利的点。任何经济体在任何时期都能找到一些领域性的问题。如果经济决定论要严肃一点,就必须具备可证伪性。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尽管2008年经历了一次惨烈的经济崩溃,爱尔兰今天的富裕程度依然比几代人之前高得多,但这种富裕却未能显著提升那些主流政治势力的声望,而正是他们主导了爱尔兰的大部分经济成功。
还有其他事实不容忽视。
特朗普分别在高通胀时期(2024年)和低通胀时期(2016年)当选总统。民粹主义者在有巨大收入差距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如美国)中兴起,但同样也在社会民主国家(如法国)中崛起。
2016年的英国,失落的年轻人选择了支持“留欧”这种维护现状的立场,而拥有资产的老年人则选择了“脱欧”这种破局之举。经历了过去十年经济创伤、原本有理由转向极端政治的希腊,如今却有一位公认温和派的总理。
而意大利,在经历较少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却选择了一个民粹主义领导人。
不仅经济状况和政治选择之间没有稳定的关联性,甚至连一个可以大致描述趋势的“最佳拟合线”都不存在。
如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那选民究竟在不满什么?
很大程度上是移民问题。但即便是移民问题也不是绝对的关键因素。为什么民粹主义在移民率高的澳大利亚没有大行其道?(在那里,也许经济确实解释了很多问题。)
法国极右翼势力的强大,似乎与外来人口规模不相符——按西欧标准来说,法国的外来人口比例并不算特别高。
另一个解释是所谓的“享乐调整”。随着收入增加,期望值也随之提高。选民变得更容易反叛。
换句话说,经济确实重要,但方式与你想象的不同。
无论如何,本世纪的美国故事,应该让那些认为政治是经济衍生品的人深思。在美国,经济可以快速增长,可以从零开始建立全球最强大的企业——但却依然可能让图尔西·加巴德这样的政治人物有机会步入重要的公职。
经济决定论之所以让人感到安慰,是因为为每一个问题提供了教科书式的答案:通过增长解决问题。
投资。这是拜登主义的核心。事实上,这也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这种逻辑有着无可挑剔的常识性,但也显得思想僵化。
相比之下,保守派更快地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比物质利益更为奇特的驱动力,并试图掌握它们。
写这篇文章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增长怀疑论者,好像会引用罗伯特·肯尼迪那种略带中学生毕业演讲风格的话,谈论GDP无法衡量的东西(比如“我们婚姻的坚固程度”)。所以要声明一下,我是增长的狂热支持者。
我希望伦敦有2000万人口,而不是1000万。但增长的理由必须是本身就有益处,更多的资源为更多的人带来价值,不是因为增长一定会带来更健康的政治。
如果曾有证据支持这种假设,现在也变得更加模糊了。
事实上,经济表现和政治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在两个方向上都崩溃了。一方面,一个国家可以拥有蓬勃发展的经济,但政治上并没有明显的益处。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可以在糟糕的政治环境下,依然不对经济造成损害。
在这一年即将结束之际,人们总会被提醒,金钱无法买到生活中的一切。要在“爱”和“阶级”之外,再加上“社会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