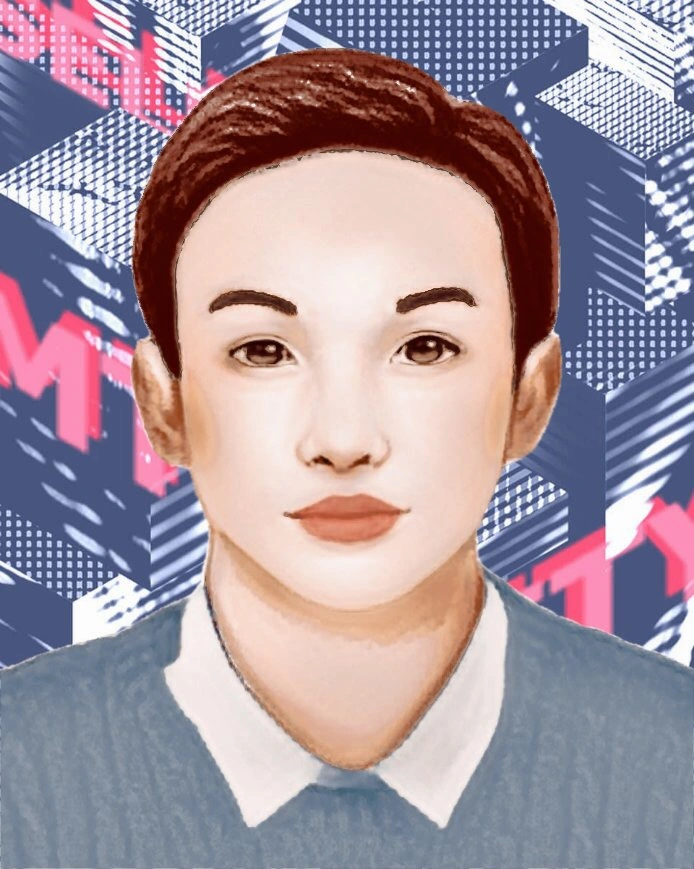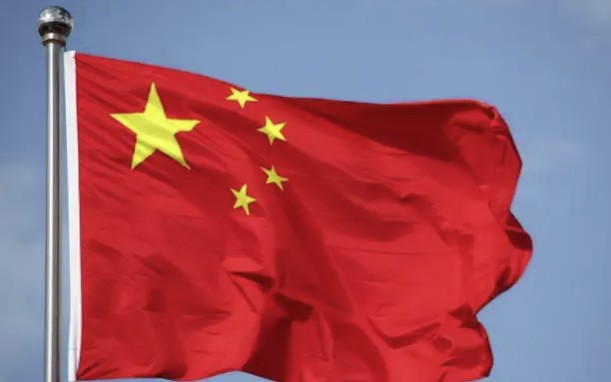这是在“向西方投降”、比经济停滞更加危险!美媒:习近平的经济困境的毛主义根源
FX168财经报社(香港)讯 哈佛商学院副教授杰里米·弗里德曼(Jeremy S. Friedman)周四(11月2日)在美国《外交政策》发表题为“习近平的经济困境的毛主义根源”。文章指出,北京方面需要国内消费者增加消费,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意识形态正在成为阻碍。

(截图来源:《外交政策》)
弗里德曼写道,不久前,专家们还在讨论中国不可避免的崛起所带来的后果。然而,今天,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放缓到一些人开始怀疑它是否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在以前似乎已成定局。话题突然转向“中国见顶论”,以及华盛顿和世界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衰落。
许多人试图解释中国出了什么问题——从新冠清零政策的冲击,到去全球化的重击,再到与美国的贸易战。一些人只是认为中国是“独裁政权一般逻辑”的受害者。
最令人信服的解释之一是,中国只是达到其以投资为主、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的极限——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所采用的一种解释。中国领导人当时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增加国内消费,中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依赖于外国消费者借债购买中国商品。
开创自由化新时代的希望破灭
尽管前任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出了名的不成功,但许多人希望,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上任时,他能做到其他人没有做到的事情。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习近平似乎是一位“雄心勃勃、注重效率的经济改革者”,将开创一个自由化的新时代。
但弗里德曼指出,习近平通过加倍实施国家主导的、以投资为主的战略,使这些希望破灭。该战略主要内容包括对内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和对外的“一带一路”倡议。
近年来,习近平的战略非但没有开放市场,反而扼杀了私营部门,导致资本净流出中国。尽管在他的任期内经济增长有所下降,但中国共产党仍将其标榜为“更高质量”的增长,这将避免不平等加剧和生态破坏等权衡。
但今天,在经济增长依然缓慢、青年失业危机和房地产行业债务负担可能引发更大范围金融崩溃的情况下,评论人士再次呼吁习近平解决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国内消费基础不足。
然而,这些呼吁不太可能得到重视。但对于习近平来说,促进国内消费不仅仅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疏忽;这样做会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愿景相冲突。当习近平看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都受到与美国意识形态冲突的威胁时,国内消费的治疗对他的中国愿景的生存来说比经济停滞的疾病更糟糕。
上世纪60年代,当苏联和中国从盟友变成死敌时,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是关于共产主义的本质。赫鲁晓夫在1961年的苏联共产主义建设计划中,特别强调消费和生活水平是衡量共产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
赫鲁晓夫认为,在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条件下,普通的苏联公民将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生活得更好。但毛泽东认为,任何在生活水平上与资本家竞争的企图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失去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超越资本主义,而是创造一个“新人”——不是由个人消费驱动、而是由共同利益驱动。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采取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他相信“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的”,并以鼓励私人企业的扩张而闻名,他说“致富光荣”。他的继任者江泽民和胡锦涛延续了这一方针,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出口大国,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之后。
在2008年之前的几年里,围绕中美关系的讨论被“金融恐怖平衡”和相应的相互依赖状态所主导——中国依赖美国消费者,美国依赖北京购买其主权债务,这一体系被学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称为“中美国”(Chimerica)。
2008年金融危机后,胡锦涛批准了一项针对国内基础设施的庞大刺激计划,希望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这一举措暗示着中国承认,如此严重地依赖美国消费者为中国的工业化买单——而且是依靠信贷——是不平衡的,也是不可持续的,确保未来增长的唯一途径是提高国内消费。
然而,对北京方面来说,纠正路线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尽管中国官方拥抱社会主义,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开放期间,为公众提供医疗、教育和养老金等福利的国有部门被掏空,而国家将增长的努力集中在出口生产上。中国家庭需要为医疗、教育、退休和其他必需品储蓄,而不是把钱花在消费品上。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在重建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几乎无所作为;因此,被吹捧的再平衡从未实现。
当习近平上台时,许多人希望他会深化中国国内的市场改革,为经济提供所需的消费刺激。在2013年的一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国家需要更多地回归“监管”角色,为市场发展提供更多空间。
习近平当时似乎也有同样的看法。在他担任国家主席的第一次演讲中,习近平说:“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享受富裕的生活,实现梦想,共同受益于国家的发展。”
但是,习近平似乎也和毛泽东一样,对不受约束的私营企业的危险持有疑虑。相反,习近平把精力集中在进一步集中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
习近平在这些努力中的优先事项往往反映出一种对避免“苏联式崩溃”的痴迷。中国共产党仔细研究了苏联的垮台,以避免自己出现这样的结果。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苏联解体的分析把大量注意力放在计划经济的问题上,以及计划经济未能为人口提供充足的供应,这使得拥抱市场改革成为维护政治稳定的合理途径。
然而,在习近平时代,对苏联解体的诊断反映不同的优先事项,变得越来越狭隘,并首先集中在一个因素上:意识形态。根据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学者的说法,苏联的解体是因为其执政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失去信心,变得自满和腐败,从而与人民失去联系,而人民也同样不再相信党的意识形态。这种内心的恐惧又被当时的全球事件加剧。
在“阿拉伯之春”和苏联解体后的颜色革命之后,莫斯科和北京都认为西方正在利用民主化来削弱其敌人,而他们是头号敌人。人们普遍担心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颠覆,尤其担心习近平会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
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对商界领袖也产生寒蝉效应
因此,习近平似乎认为,重申党的作用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活力是比进一步推进市场改革更紧迫的任务。他的统治始于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运动,清除可能对习近平不忠的前任领导人手下的潜在竞争对手和官员,这不仅对政府产生寒蝉效应,对担心被卷入这场清洗的商界领袖也产生寒蝉效应。
这场运动也是为了净化中国共产党,恢复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新尝试,打击“历史虚无主义”,并增加党的在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包括通过在私营企业中安置党支部,以帮助确保私营部门的决策与中国共产党的目标相协调。
与邓小平不同的是,习近平接受了一种明显的毛式社会主义,强调个人为集体利益而牺牲,这让人回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恶化,习近平越来越强调这种方法。他鼓励中国年轻人“吃苦”——换句话说,牺牲和努力工作以获得更少。
习近平批评当今年轻人的道德品质和职业道德。这些人普及了“平躺”等概念,拒绝激烈的职场竞争,赞成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
促进消费是在意识形态上“向西方投降”
习近平的政府还发起一场复兴传统男子气概的运动,试图将“娘娘腔的男人”从公共领域驱逐出去,接受毛时代的保守禁欲主义。由于担心电子游戏可能对中国年轻人的道德素质产生有害影响,他的政府也试图限制电子游戏。
简而言之,习近平的社会主义不是富裕的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这似乎是一种道德上的社会主义,源自他年轻时的毛主义价值观。
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不仅仅是为了吓唬民众,让他们默许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只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党内和社会中充满活力的情况下,党的控制才是可行的,而对个人消费的关注不利于这种活力。
弗里德曼称,鉴于习近平对中国面临的危险的信念,他极不可能愿意让中国经济朝着个人消费的方向再平衡,即使他知道怎么做。
对于习近平来说,这无异于为了拯救村庄而烧毁村庄。相反,习近平更有可能采取不温不火的供给侧政策,动员越来越多的失业青年为某些政党主导的事业而努力,同时对破坏他声称所推崇的职业道德的各种表达形式进行政治打压。
习近平的地缘政治伙伴、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和伊朗总统莱希(Ebrahim Raisi)也将西方价值观的扩张视为对其政权的根本威胁。但是,当普京和莱希利用促进消费的政策来赢得民众支持时,中国领导人却放弃这么做。作为唯一一个仍然正式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国家,习近平对西方价值观的解读似乎带有明显的唯物主义色彩。
弗里德曼在文章最后写道,对习近平而言,促进消费被视为在意识形态上“向西方投降”,这对他的政权来说比经济停滞更加危险。
交易商排行
更多- 监管中EXNESS10-15年 | 英国监管 | 塞浦路斯监管 | 南非监管92.42
- 监管中FXTM 富拓10-15年 |塞浦路斯监管 | 英国监管 | 毛里求斯监管88.26
- 监管中GoldenGroup高地集团澳大利亚| 5-10年85.87
- 监管中金点国际集团 GD International Group澳大利亚| 1-2年86.64
- 监管中Moneta Markets亿汇澳大利亚| 2-5年| 零售外汇牌照80.52
- 监管中IC Markets10-15年 | 澳大利亚监管 | 塞浦路斯监管91.81
- 监管中CPT Markets Limited5-10年 | 英国监管 | 伯利兹监管91.56
- 监管中GO Markets高汇15-20年 | 澳大利亚监管 | 塞浦路斯监管 | 塞舌尔监管87.90
- 监管中alpari艾福瑞5-10年 | 白俄罗斯监管 | 零售外汇牌照87.05
- 监管中易信easyMarkets15-20年 |澳大利亚监管 | 塞浦路斯监管86.33